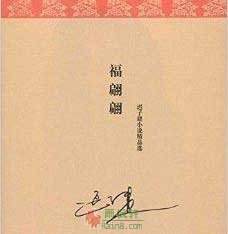
天还睡着呢,柴旺家的就醒了,她怕惊醒柴旺,便抱起被子底下的棉袄棉裤,下了炕,摸到鞋,提着它们到西屋穿戴去了。昨夜炉子断火早,屋子冷飕飕的,柴旺家的光脚走在水泥地上,就有踏着霜的感觉。她鼻腔发紧发痒,知道是喷嚏在里面鼓噪,便用棉袄掩住口鼻,三步并作两步地快走,忍到腿迈进了两屋的门槛,才把喷嚏打到棉絮里。
柴旺睡着,他有理由睡得沉,昨晚他吃了两样好饭呢。
第一样好饭是端到桌子上的一锅肉片酸菜粉丝汤。后院的王西林家宰猪,柴旺家的打开钱匣,手指在一堆花花绿绿的钱间抖来抖去的,想到狱中的儿子时就合上了钱匣,可一想到柴旺消瘦寡黄的脸时,又忍不住掀起钱匣的盖儿。最后她还是摸出十块钱,买回一窄条五花三层肉,连着皮切成均匀的长条,加上花椒大料、蒜瓣葱段,用白水清煮。她没有炝锅,一是为了省点豆油,二是觉得肉里存着肥油,慢火煎熬后,油星自然会抽身而出,一颗颗泛起,汪在汤面上。当油星越聚越多,汤面有了星空的气象时,柴旺家的从缸里捞出一棵酸菜,切成丝,投进锅里。美艳的肉条和暗淡的酸菜在炉火的煽动下,开始了不间歇的亲吻。肉香味飘了出来,汤汁也逐渐缩紧了,这时再把一绺白胡子似的粉丝撒进去,看着它由僵硬变得柔软,通体透明,像一缕缕光把汤照亮时,就可以把汤锅从火炉上撤下来了。
柴旺每天出去找活儿干,总是天黑了才回。好像一个靠力气吃饭的男人,若是在天光明亮时归家,就是无能和懈怠的表现。不管柴旺这一天揽没揽到活儿,挣没挣到钱,只要看见丈夫踏进家门,柴旺家的心里就会泛起一股怜惜之情,赶紧把温热的洗脸水端来,让他洗去一天的风尘;再把饭菜摆上桌,让可口的饭食除去他身上的寒气或暑气。当然,隔三差五的,他们也会相拥着,在暗夜中合唱一折“鸳鸯戏水”的戏,然后心满意足地睡去。柴旺向老婆求欢的时候,通常会说,我想吃“那一口”了。
昨晚,柴旺蹬着三轮车回来,看到老婆端上桌的那锅肉片酸菜粉丝汤,就像被阴雨笼罩了多日的人突然看见了太阳一样,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他们守在锅前,一碗连着一碗地畅快地吃,汤锅见底儿了,柴旺身上的另一种力气也滋长起来了,他在老婆洗刷碗筷的时候说,我要吃“那一口”。柴旺家的嗔怪道,我就知道,给你吃了“这一口”,你就会想着“那一口”!柴旺嘿嘿笑了,说,还不是你把我的那根馋虫勾引出来了?
柴旺家的在灶房洗碗的时候,看着炉火将熄,没有再往里面添柴。一则为了省点柴火,二则吃“那一口”的时候,屋子凉些才好,这样两个人会更紧地搂抱着,不舍得分开。果然,柴旺吃第二样好饭的时候,把柴旺家的紧紧箍在身下,说不出的缠绵和热火。
柴旺家的调理男人的手段除了这两样好饭外,还有一着,就是称谓上对男人的依附。她原本叫王莲花,可自从嫁给柴旺后,就让人们唤她柴旺家的。她那伶牙俐齿的姐姐王莲蓉曾挤兑她说,你也真没出息,嫁了个男人,把名字也给嫁丢了!王莲花笑着对姐姐说,女人嘛,进了谁家的门,就是谁的人了。随着男人的名字叫,他会觉着得到了一个宝,要好好爱惜着。他会拼了力气让这个家过得好的!王莲蓉一撇嘴说,什么宝,再好的女人,不管进了谁家的门,头三年是宝,接下的三年是草,余下的日子就是糟糠了!王莲花不在意姐姐的讥讽,照样有滋有味地当她的柴旺家的。这二十年过下来,虽然生活有那么多的不如意,但柴旺还是柴旺,她也仍然是幸福的柴旺家的。倒是姐姐,那个近五十岁了还要强迫丈夫唤她昵称“蓉蓉”的王莲蓉,虽然衣食无忧,但感情上却很落寞,男人四十多岁时就萎靡了,近些年她等于是守着空房。
柴旺家的穿戴好,来到户外。北风吹着,黎明前的星星虽然稀少了,但留在空中的每一颗都异常明亮。柴旺家的喜欢把星星联想成一簇簇火花,她想自己要是能摘下几朵多好啊,把它们放在炉膛里,永恒地燃烧着,发出光和热,省却了她为柴火操心。
邻居刘老师家的狗听见动静,知道是柴旺家的出来了,便温柔地狺叫了几声。柴旺家的隔着板障子冲那院说,空竹,我去北山搂树皮去了,你可得帮我看着点院儿啊。狗“唔唔”哼着,似是答应。柴旺家的从仓棚拎出两条麻袋,叠好,夹在自行车后座上,又把一个铁挠子插在车把的篮筐里,推着自行车出了家门。
腊月天,刀子天;腊月风,似鞭子。风把屋顶的雪搅扰得四处飞扬,让人以为下雪了。坑洼不平的巷子里一个行人也没有,柴旺家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,自行车则跟着高一脚低一脚地“哐啷——哐啷——”地叫着。上了水泥马路后,柴旺家的跨上自行车,可她行进得很艰难,一是迎着风走,阻力大;二是天太冷了,车链冻僵了,蹬起来滞重。柴旺家的索性跳下车,推着走,反正天还没大亮呢,回去做早饭还来得及,再说步行身上还暖和。
柴旺家住在城西。这座县城不大,只五万多人口。城区主要分四部分:主城区、次城区、城东和城西。主城区是清一色的楼房,政府的主要机构和两个大的购物中心均设置在那里;次城区也是楼群,不同的是衙门少,商铺多。商铺多的地方人气旺,所以这一部分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城东呢,是楼房和平房交织处,县里的重点高中建在那里,虽然有些零乱,但还是充满了生气。只有城西,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平房,这一带原来有两家大厂子,一个是机修厂,一个是造纸厂,如今造纸厂黄了,机修厂也因经营不善,缩减了规模、裁减了人员,所以住在这一带的工人多半都下岗了。一个散发着清贫之气的地方,商业自然会不兴,这里只有几家小的杂货铺和连幌子都不需挂的小饭铺。
柴旺家住在城西,已经有三十几年了。他年轻时在机修厂当车工时,就和母亲住在这里。母亲过世后,他又从这里把王莲花迎娶进门,生下了儿子柴高。王莲花喜欢柴旺的忠厚,更喜欢他那一身的力气。她爱上柴旺,是因为一块石头。那一年秋天家里多腌了一缸酸菜,缺一块压酸菜的石头,王莲花就骑着自行车,去城西的乌吉河寻石。机修厂就在乌吉河畔,每到夏日的正午,吃过饭的工人们喜欢到河边洗澡、晒太阳、打扑克。秋天时,他们爱玩儿“打水耗子”的游戏。几个人围成一圈,抓阄选中一人当水耗子,把他圈在中央,给他三分钟时间,如果他能突出重围,每个人要敬给他一支烟,如果他失败了,就把他扔进河里,让冰冷的河水鞭挞他。那天王莲花来到河边,正好看到一群小伙子在玩儿“打水耗子”。被困在中央的正是柴旺。天已经凉了,可他光着脊梁,他发达的胸肌让她感觉那是一架动力十足的机器,发出强劲的轰鸣声。柴旺虽然中等个,但他弹跳好,没用上一分钟,便纵身一跃,像匹奔马一样,从圈里轻盈地跳出来。人们给他敬烟的时候,王莲花从他们身边经过。王莲花把自行车放在河滩上,去水里寻石头。她看上了一块菱形的青石。它离河边也就一米多远,在浅水中。王莲花卷起裤管,下了河。从岸上看水中的实物,往往容易看走了眼。远看它不大不小,可真正切近它时,才发现它很厚重。是水上的波纹充当了美容师的角色,为它瘦了身。王莲花试探地搬了几次,它只是微微动了动,算是跟她点过头了。王莲花那年二十二,一身的力气,她犯了倔劲,心想我就相中你了,一定要把你弄回家。她使出全身力气,终于勉强搬了起来。她咬着牙,哆嗦着走了两步,那块石头还是从她怀中挣脱了,“扑通”一声回到水里,溅起一片灿烂的水花。岸上的小伙子们都笑了。柴旺也笑了,不过他不像其他人只是看笑话,他下了河,帮王莲花把石头搬上岸。那块对王莲花来说不堪重负的石头,在柴旺怀里就像一个乖巧的婴儿,服服帖帖的。他很轻松就把它放在了王莲花自行车的后座上。怕那石头在路途中遇到坎坷会被颠簸下来,柴旺又顺手掳了几把草,两三分钟便拧成一根草绳,把石头捆牢了。王莲花推着自行车离开河滩的时候,对柴旺说,我叫王莲花,你要是有难洗的衣服,我帮你洗!柴旺笑了,说,我有一件帆布工作服,一直没有洗透亮过。王莲花说,那明天中午我带着肥皂来,你把衣裳给我拿来!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