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震亨与张岱,晚明文人的生与死
时间:2017-02-21 作者:潘向黎 点击: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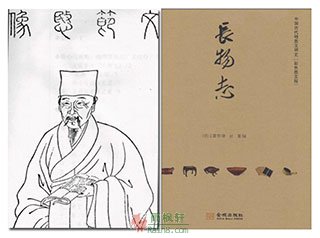 《长物志》以前随手翻过,有一天突然心里安静,细细再看,才看出好来。也才看清楚了作者:作者文震亨,竟是“明四家”文徵明的曾孙。因为到苏州博物馆看过文徵明的书画展,心里便对文震亨也亲近了几分。
且看他是如何人物。文震亨(1585年-1645年),字启美,江苏苏州人,生于明万历十三年,明天启六年选为贡生。曾参与五人事件,营救被魏忠贤迫害的周顺昌。崇祯年间为中书舍人,武英殿给事。曾任职于南明。
文震亨家富藏书,诗文书画俱闻名于当时,善园林设计,著有《长物志》十二卷,为传世之作。并著有《香草诗选》、《仪老园记》、《金门录》、《文生小草》等。其山水画师法宋元诸家,韵格兼胜;其小楷清劲挺秀,刚健质朴,一如其人,据说既有其曾祖父所开之家风,又吸收了欧体的某些笔法与结体。这样的字,字如其人,其人其字,都是很高的评价了。
且看他如何结局。弘光元年(清顺治二年,1645年),清军攻占苏州后,避居阳澄湖。清军推行剃发令,他宁死不从,自投于河,被家人救起,忧愤绝食六日而亡,终年六十一岁。“士可杀不可辱“,他以生命践行了,而且践行得如此天经地义。这种源于文化、来自人格的亮烈和凛然,是多么令人仰望而心折。“自古好物不坚牢”,由此带来的脆弱的生存基础,又多么令人惋惜和心痛。
“文震亨生于名门,聪颖过人,自幼得以广读博览,诗文书画均得家传。其人‘长身玉立,善自标置。所主必窗明几净、扫地焚香’以琴、书名达禁中,‘交游赠处,倾动一时’。……(《长物志》)表面上,这是对晚明文人清居生活方式的完整总结,反映晚明士大夫的审美趣味,然而对文震亨而言,更重要的是寄托他‘眠云梦月’‘长日清谈,寒宵大坐’的幽人名士理想,不食人间烟火。”(海军 、田君注释、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《长物志图说》卷前《格心与成物:晚明景象的广义综合》)
文震亨这个人,在我面前立了起来,长身玉立,神情淡漠下掩着凄然与孤绝。一身才艺,唯美洁净,孤标傲世,拒绝污浊,绝不妥协,这样的人,在时代的大动荡中怎么活啊?所以他果然活不下去了。说殉国当然可以,但其实,不如说是一个嗜美如命的人,殉那些精致、隽秀、美妙的事物;一个不洁净就不能活的人,殉他洁净讲究的风雅和被毁了的理想生活。
心痛如割。这样的一个人,完全应该和他的曾祖父一样,尽其才,得大名,享高寿,可是仅仅因为生在那个年头,就落得了这样的结局。 什么都没有做错,却落得了这样的结局。
这样的一个人,落得了这样的结局。这样的一个人,竟落得了这样的结局。
张岱也是生在那个遭遇巨变的时代,张岱“学节义不成”,因此没有死。这位“好精舍,好美婢,好娈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,书蠹诗魔”的世家子,“年至五十,国破家亡,避迹山居,所存者破床碎几,折鼎病琴,与残书数帙,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,常至断炊。”“国破家亡,无所归止,披发入山,駴駴为野人。故旧见之,如毒药猛兽,愕窒不敢与接。作自挽诗,每欲引决。”
谢谢张岱的“软弱”,这位不世出的妙人终于勉强活了下来,又在万念俱灰之中,出于一种补偿心理,出于一段痴情,记下了他的繁华旧梦,令后人每读之都口角噙香、心驰神往。
除了个性的差别,我无端猜测张岱的长相大概不如文震亨。家世、富贵、相貌、才情,文震亨样样俱全,这样的人,最好迟钝一点,混浊一点,年轻时混成一个声色犬马的混世魔王,老了硬充一个庸俗而满足的十全老人或者八全老人,也就罢了。他偏偏不肯,偏偏冰雪聪明,偏偏事事那么有原则,样样那么精细,如此极致,岂能久长。人世容得下,天也容不下。
张岱大概就是缺了一个好相貌,缺了这一角,有些方面可能也比文震亨略圆通随俗些,总算得以保全性命于乱世。保全是保全了,想到他后来那样的活法,也还是令人心痛。就像一个正在自己家捧着精致美味吃喝得眉开眼笑的孩子,被一个粗蛮外人冲进来,一巴掌打碎了碗,害他跌坐在一地狼藉之中那样。
由相貌而论气数,实在是容易越说越宿命,那么说回现实的话题,如果,文震亨被迫剃了头,并且捱过了受辱的第一波创伤应激反应,进入以诗文或者绘画创作来自我排解自我救赎的阶段,会不会不但活下来,还给我们的文学史或者绘画史增加一个精彩章节,给我们这些后人多留一部(或一些)赏心悦目、击节赞叹的作品呢?
很有可能。理应如此。可惜这只是一个善良而无力的假设。
当然,写再好的作品,对于当时的他们自己,都是没有用的。就像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,后世的无数激赏和眼泪,都不能化作当时的一碗碧粳米熬的粥,热热地给他充饥,更不要说变成一碗小荷叶小莲蓬的汤,鲜香扑鼻地让他解馋。
寂寞身后名,而当时的天大的难,无边的苦,无休无止的痛,都是要一个个的人,作为生命个体,自己面对自己扛的。
今天读《长物志》《陶庵梦忆》,多少心会多少赞叹都安慰不了他们,连我们爽快买书的钱也并无一毛钱可以救济到他们。
酒一滴都不到刘伶坟上土,那么眼泪呢?异代同调、无限痛惜的眼泪和哭声呢?能不能穿透干冷硬化的时间,穿越到那时那刻,安慰一下文震亨和张岱那海沟一样深的绝望?那样慧敏的人,那样多情善感的人,他们也许这样莫名地指望过?
说不定,他们这样坚信过:安慰和温暖会来的,哪怕隔了生死,隔了朝代。也许,这就是那样的人,遭逢那样的命运,依然写作的原因呢。 |